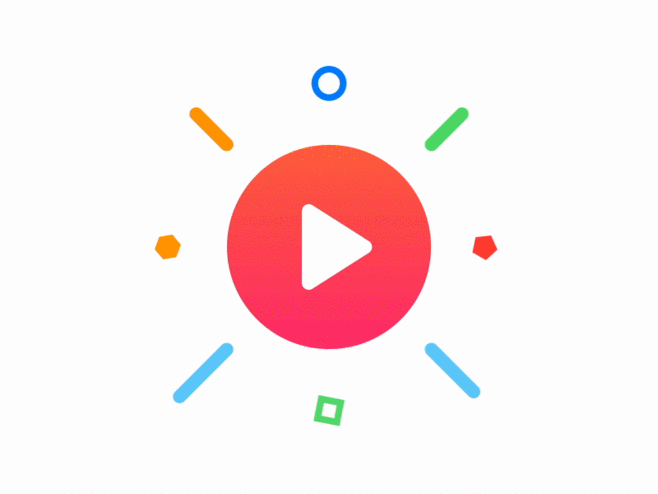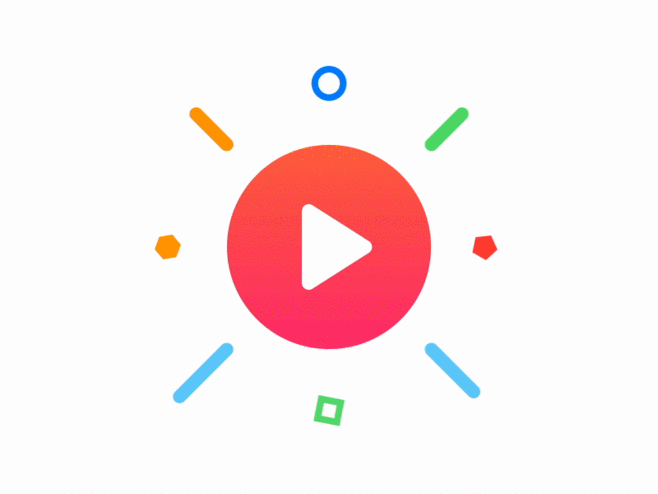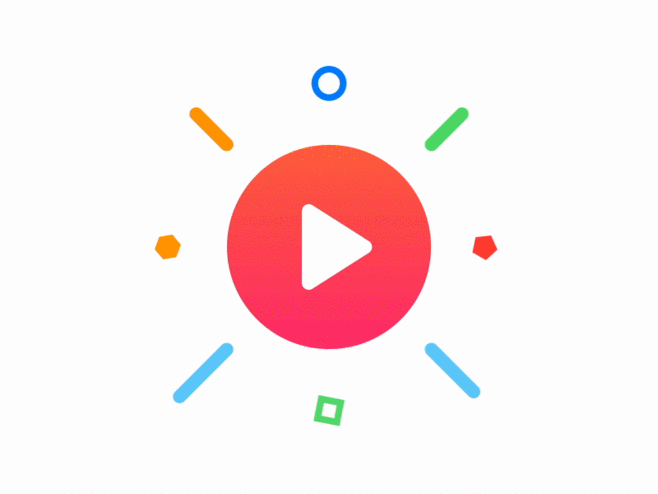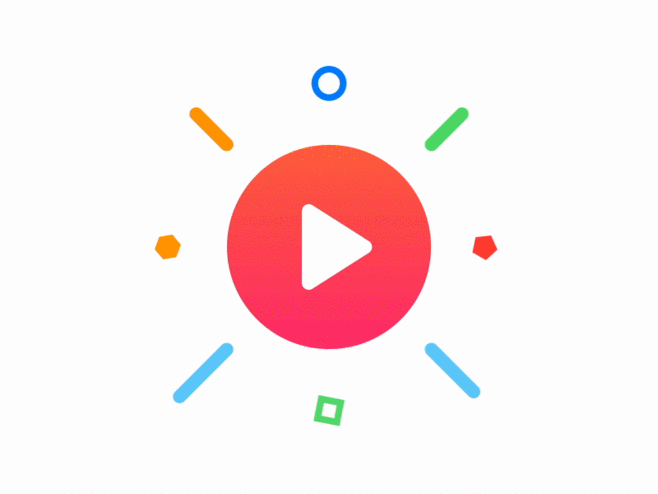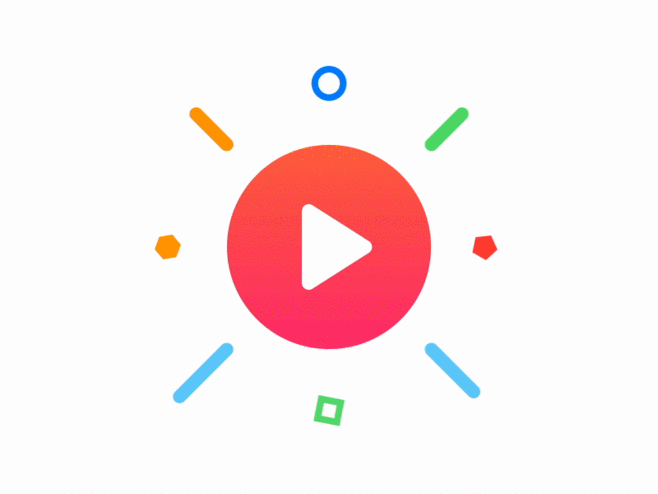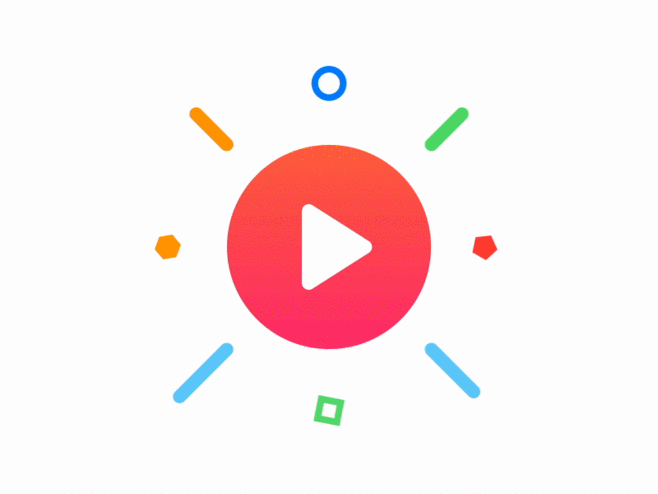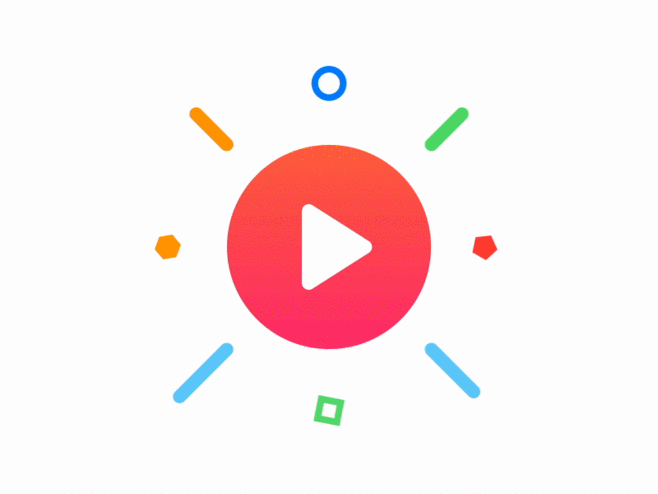人為什么會得強迫癥
- 瀏覽量:1752
- 來源:中華名師網
- 2015-03-13
一個叫碧拉的埃塞俄比亞女孩吃掉了家里一整面墻。她不想吃,但她控制不住自己——她無時無刻不想著那面墻。將土墻上的泥摳下來吃掉,是她唯一的解脫方法。
這事持續了十多年,到17歲時,她吃掉的墻面共有8平米。她的胃部嚴重受損,喉嚨破裂,體內爬滿寄生蟲。痛苦不堪的碧拉終于去看了醫生。醫生告訴她,她需要幫助。
這個故事出自一本書——《無法停止的人:強迫癥及一個迷失在思緒中的真實人生故事》。2015年1月底,它在美國出版。書的作者大衛·亞當(David Adam)曾是英國《衛報》科學與醫學記者,現為世界頂級科學雜志《自然》編輯。這本書出版后大受好評,英美主流媒體紛紛稱贊它是一部關于強迫癥的力作,包含了大量案例和深入淺出的科學分析,又從個人視角寫了一個令人動容的人生故事。
針對此書,騰訊文化作者對亞當進行了電話采訪。亞當說話很輕,有淡淡的英國口音。談起強迫癥給他帶來的困擾,他有一種就事論事的平和。的確,強迫癥的成因極其復雜,醫學界迄今無法給出定論,患病在某種意義上給人“中彩”之感。對亞當來說,重要的是直面病情,以理性的態度尋求幫助和治療。
亞當本人的強迫癥是從19歲開始的。1990年的某個秋夜,亞當與一個美麗的女孩約會。當天他們并未發生關系,但為了向朋友吹噓,亞當撒了謊,并稱他沒有使用避孕套。
“你可能會得艾滋!”朋友說。這個想法就此在亞當腦海里種了下來,揮之不去。舊牙刷、垃圾桶里沾了血跡的紙巾、朋友手上的創可貼……他開始覺得,看到的一切都和艾滋有關。他需要一遍又一遍地檢查和確證自己沒有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。
如今,強迫癥已陪伴了他二十多年。他的每一天都在恐懼與焦慮中度過。他會仔細檢查自己接觸到的一切東西,隔三岔五去驗血,不敢去公共游泳池。強迫癥極大地占據了他的精力和注意力,讓他疲累不堪。
但亞當很好地藏起了自己的焦慮和恐懼,一瞞就是二十年——“艾滋病”總讓人覺得與性相關,他難以啟齒。盡管作為科學記者,他知道這想法是非理性的。
常人對強迫癥有重大認識誤區
在書中,亞當貢獻了不少名人的例子。比如,被稱為“交流電之父”的發明家尼古拉·特斯拉害怕病菌,為此不與朋友接近,獨自在酒店住了十年。他還癡迷數字3,因此住在曼哈頓紐約客酒店33層的3327號房間。
再比如,童話大王安徒生的恐懼是睡覺時被人活埋。每晚睡覺前,他都要在床頭留一張紙條,指出他是在睡覺,不是一具死尸。
人為什么會得強迫癥
亞當告訴騰訊文化作者,大多數人都聽說過強迫癥,但對它的理解比較初級。大部分人認為,強迫癥患者會經常洗手,出門前一遍遍檢查門窗是否鎖好,或是反反復復關燈。的確,最常見的強迫思想是害怕細菌感染,約三分之一的強迫癥患者屬于此列。其次是對危險的非理性恐懼——重復性關門和關燈的人屬于此列,占患者總數的四分之一。再次則為對圖案及對稱的強迫性需要,占患者總數的十分之一。
人為什么會得強迫癥
過于頻繁地洗手,是最常見的強迫癥癥狀之一。
人為什么會得強迫癥
對圖案和對稱的需要,是另一種常見的強迫癥癥狀。
人為什么會得強迫癥
對顏色的需要,也是強迫癥癥狀。
人為什么會得強迫癥
瑞士攝影師烏瑟斯·威利是一名整理強迫癥患者。圖為其作品。
這些小習慣的確挺煩人,但在大多數人看來,它們不會對生活造成太大影響。人們對強迫癥存在太多認識誤區,最主要的是,許多人都將它看成一種行為怪癖,沒有意識到它其實是一種嚴重的精神疾病。
事實上,強迫癥的形式多種多樣,有些“怪癖”足以致命。亞當說,馬庫斯是一個巴西男人,他總覺得自己眼睛的形狀不對勁。為了壓制這種思想,他不斷用手指去觸摸自己的眼睛,最終把自己戳瞎了。
而愛因斯坦的好友庫爾特·哥德爾是杰出的數學家,提出了著名的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。他害怕食物中毒,因此從不碰妻子沒有事先試吃過的食物。妻子病重后,他在美國普林斯頓的醫院絕食而死。
人為什么會得強迫癥
亞當告訴騰訊文化作者,不僅一般公眾對強迫癥有誤解,許多患者對它的了解也不多。究其原因,如果不去看醫生,患者的信息源和普通人是一樣的。“假如你認為強迫癥就是經常洗手或開關DVD機,而你的問題是你常常有傷害別人的想法,你就很難意識到自己患了強迫癥。”
強迫癥的英文名為Obsessive-Compulsive Disorder,簡稱OCD。它包括兩部分:強迫思維、強迫行為。以經常需要洗手的人為例,強迫思維是這個人總擔心碰到臟東西會得病,強迫行為則表現為不斷洗手。洗手是為了減輕強迫思維帶來的焦慮。
亞當的強迫思維是關于艾滋病的恐懼,他的強迫行為是通過種種方式緩解這種恐懼——拒絕與手上貼創可貼的人握手,拒絕與人共喝一瓶水。
有一段時間,他瘋狂地撥打艾滋求助熱線,向接線員講述自己的恐懼。接線員一再告訴他,得艾滋病的幾率極低。有那么一會兒,他覺得好受些了,但是等等——“幾率極低不代表沒有可能。”懷疑的聲音很快冒出來,他需要再次尋找確證。那段時間,他過于頻繁地撥打求助熱線,所有接線員都記住了他的聲音,他只好一再冒充別人、用別的方言打電話。
強迫癥患者的難處:難以啟齒
強迫癥的一個關鍵危險是,患者往往拖延治療。“在確診和治療之間,普遍存在十年的間隔。”亞當說。這是一個驚人的時間差。究其原因,亞當稱,在他那里,主要不是因為無知,而是很難去直面它。
為什么強迫癥讓人這樣難以面對呢?亞當分析,盡管醫生再三告訴他應該接受治療、能夠獲得幫助,但他的那些情緒和想法如此強大、如此根深蒂固,他覺得它們永遠不可能消失。
向別人講述自己的心理疾病是困難的,而且許多患者執著的東西恰恰是社會公認的禁忌話題,例如性、傷害、死亡。在患者能隱瞞病情的情況下,自然也就沒有外在壓力促使他去尋求幫助。而因為許多患者將病情掩飾得很好,身邊人也很難向他們提供幫助。
亞當花了20年時間才向父母坦白自己的病情。在和出版社簽了書約后,亞當要求出版人對消息保密,因為他要先告訴父母——他不希望他們通過新聞知道這個消息。對亞當來說,承認自己的癥狀其實是一種“出柜”。
亞當認為,“出柜”一詞很好地描述了這一舉動。就像同性戀一樣,許多強迫癥患者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,怕被用有色眼鏡看待,怕在交友、求學、求職時遭遇不利。盡管“教育公眾”不是他最初的寫作目的,但他的書無疑有助于增加公眾對強迫癥的認知度、對強迫癥患者的同情與理解,從而創造一個對患者的生活與治療有利的環境。
亞當認為,強迫癥的最大傷害是對他情緒狀態的影響。“有關艾滋病的恐懼總在我腦子里,占據了我本可以放在別的事、別的人上的注意力。”亞當會幻想,如果沒有得強迫癥,他的某些人生選擇會不會不一樣。“我記得我沒得病之前的樣子。我嫉妒從前的自己。”他說。
人為什么會得強迫癥
人類對強迫癥的認識起步很晚,直到1980年代,精神科專家還認為強迫癥的案例不多。如今,醫學界普遍認為強迫癥是四種最常見的心理失調癥狀之一,排在抑郁癥、藥物濫用和焦慮癥之后。世界衛生組織將強迫癥列為十大最嚴重的精神疾病之一,其發病率是自閉癥和精神分裂的兩倍。
強迫癥成因復雜,心理學界對此至今沒有定論。但研究者們從遺傳學、認知心理學、神經科學等角度考察,近年來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。
亞當認為,對強迫癥的成因需要分兩部分來看:一是什么讓人容易受強迫癥侵擾;二是什么真正觸發了強迫癥。
強迫癥對人“有機可乘”,是因為我們所有人都會產生奇怪的想法。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“侵入性思維”(Intrusive Thoughts)——許多人都有過搶劫、傷害他人、從高處跳下、偷看陌生人裸體的想法,這些想法無緣無故,不請自來。幸運的是,多數人的這些思維轉瞬即逝,不會演變成強迫癥。但對有些人來說,某個想法在腦中卡住了,再也無法驅走。
神經科學家對大量強迫癥患者做了大腦核磁共振成像研究,發現他們的大腦基底核出現異常。基底核位于大腦深部,目前所知的主要功能為對自主和重復運動的控制。其運作很容易被啟動,卻很難被關閉,所以不難理解為什么強迫癥會與它的異常有關。
強迫癥不僅與大腦構造相關,也與后天環境相關。童年時期就形成的某些思維傾向讓一些人更易得強迫癥,心理學家將這些傾向稱為失調信念(Dysfunctional Beliefs)。
與強迫癥有重大關系的失調信念有三種:夸大威脅與責任的傾向;完美主義與對不確定性的抗拒;將個人思緒看得過于重要,因而忍不住想要控制它們的傾向。有這些傾向并不意味著就會得強迫癥,但這會讓人過分放大那些侵入性思想。
至于是什么觸發了強迫癥,則因人而異。有些人的原因與某個心理或精神創傷有關,但沒有一個特定原因可以解釋所有案例。
強迫癥還和社會文化潮流息息相關——社會上流行的恐懼,往往在個人心中形成投射。亞當指出,在他這個年齡層的人當中,“擔心艾滋病”是極為常見的強迫癥形式之一,因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對艾滋病的恐慌最嚴重的時期。美國精神科醫生朱迪斯·瑞波波特在其名著《不能停止洗手的男孩》中寫道,到1989年,他三分之一的患者癥狀都是極端害怕艾滋病。正是這本書讓許多人第一次認識了強迫癥。
最重要的是要去看醫生
強迫癥患者經常被誤診,因為其癥狀常常被其他癥狀所掩蓋,比如抑郁、焦慮、飲食紊亂等。直到最近,人們都不太重視強迫癥與焦慮癥之間的區別,將其視為后者的一種。的確,焦慮是強迫癥的表現之一,但混淆兩者之間的差異是危險的。
今天,精神科醫生普遍將強迫癥看成一個獨立的譜系,和它放在一起的,還有一系列與侵入性思維和沖動控制障礙相關的病癥,如軀體變形障礙、囤積癥、拔毛癖、摳皮障礙等(軀體變形障礙患者喜歡想象自己的外形有缺陷并放大這種缺陷,每天花數小時在鏡子檢視自己,用化妝、假發、變裝甚至整形改變外表,有些人甚至無法出門)。
亞當告訴騰訊文化作者,對強迫癥患者來說,最重要的是認識到強迫癥是一種疾病,需要醫療救助,就像斷腿的人需要醫生一樣。
他表示,目前對強迫癥最有效的治療方法,是藥物治療和認知行為療法的結合。抗抑郁藥物中的一種——SSRI類藥物(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)——被證明對治療強迫癥有效。認知行為療法則是目前英美治療強迫癥最流行的方法之一。它認為,人的情緒來自人對所遭遇事情的信念、評價或解釋,而非來自事情本身。向患者指出其信念失調,能幫助他們重新認識自己,逐漸改變行為方式。
這項研究給亞當帶來了什么?亞當認為,研究讓他認識到強迫癥的影響廣泛,不分歷史時期,不分國籍,不分文化。他很慶幸自己在二十世紀末的英國患病,因為更深入的研究、更有效的治療方法,對他幫助極大。
他并不認為自己寫了一本自救書,但他說,將自己與強迫癥搏斗的故事寫出來,意味深遠,可以鼓舞其他患者。無疑,這本書會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強迫癥,讓人們更理性、更平和地與腦中的“惡魔”作戰。